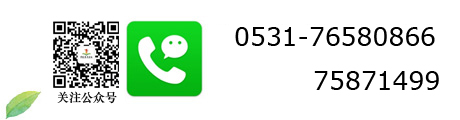○一
就在那个夏天,我经历了人生的一次大悲痛——父亲在一次车祸中走完了他43岁的生命历程。那天似乎所有的东西都黯淡了,天上的阴霾就像擦泪的手巾,微微的触动便会湿透半边天。似乎老天也承受不了这种亲人离去的悲凉,末了竟沥沥淅淅的下起雨来。
还记得当我抱着父亲血肉模糊的遗体,切身的感受到那瘦索的躯体里再没有了那种宽厚的温和,我忽然像失去了知觉,由号啕大哭变成了呆立漠然,在泪眼彷徨中,我看到了二叔和二叔在风中飘摇的白发……
在得了父亲过世的消息的那天晚上,二叔坐在父亲的灵枢前,老泪横流,直至深夜不肯离去。第二天再见他,竟然头发全白了。
其实,二叔并不是我的亲叔,他是父亲的把兄弟。
二叔和父亲在过去那个苦难岁月中所结下的情感,已经像他们手上的老茧一样,集结成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记。爱屋及乌,再加上二叔没有亲眷,于是,我很自然地便成了他精神上不可割舍的寄托。
我们那山坳里产枣子,记得儿时,我嘴馋,每每在枣子刚泛红还未熟透时,我就嘴角流着涎水吵闹着要吃枣子。每当这时,父亲是不肯搭理我的,因为这个季节的枣子是不能用长竹竿打的,那样只会折了树的“阳气”,还会损坏很多泛青的枣子。要想吃,只能爬上树去采摘。而那时的枣树上易生一种俗称“扒疥毛”的小虫,很是历害。这虫子满身毛刺,一碰上它,皮肤上刹时就会凸起一片小红疙瘩,而且像被蜂蛰一样“嗖嗖”的疼。所以,没人愿上枣树。
这时,二叔便成了我心中的大英雄。因为只有他愿意忍受被“扒疥毛”蜇着的苦痛,为我上树摘枣子。
记得又是这样一个枣香飘飞的季节,当我嘴角的涎水又开始滴滴答答地流下来时,二叔已经琢磨着为我摘
枣子了。可是,父亲却死活不让二叔再攀树,因为二叔在今年春天的一场车祸中刚刚撞折了腿,到现在腿脚依旧不灵便,父亲怕他有个闪失。可二叔的决心似乎比父亲的理由更充分。他偷偷地把我领到枣树林,让我在一棵高大的枣树前站定了,这才艰难地爬起树来。
二叔由于伤腿的缘故,动作可比平日笨拙得多。他先将两只粗糙的手紧紧贴在同样粗糙的枣树皮上,然后用右脚勾住树干,左腿却僵直地伸着(他左腿受了重创),就像一段枯死的木头。他一寸寸地向上蠕动着,所有的气力似乎都倾注在了他强壮的臂膀上。终于他的右手抓住了一段伸出的枣枝,左手紧跟着也靠了上去,他的身躯完全腾空了,腿脚失去了依托。他嘴里喊着“一二三”,臂膀和腰腿一齐用力,终于用右腿攀住了那段枝干,然后整个身子连着那条病腿翻了上去,引得那段枣枝一阵剧烈的颤动……”
虽然动作迟缓而又艰难,但终还是一点点攀上去了。他在枝上站稳了脚,就像往常一样吆喝起来“强子,想要哪个?”“我就蹦着跳着叫着用手忙不迭地指着:“这个……那边那个红点儿的……”一个个枣子便像雨点般的落了下来。
等摘的够我吃上几天的了,他也不急于下来,而是坐在一段枝上很高兴很得意很满足地看着我吃枣子时狼吞虎咽的模样。等我吃够了,他便又摘了一捧枣子,这才攀下树来,以往他攀下树时是站在枝上往下跳的,这次却不能了。他只好两手轻轻的贴住树皮,右脚勾住枝干,笨拙的滑了下来,擦了一肚皮的血痕。
当我将一个又红又大的枣子塞进二叔的嘴里时,我才发现他满脸满手的小红疙瘩,我立即明白了什么,心里顿时涌上一阵深切的歉意。但二叔似乎并不介意,只要我快乐,他就满足了。
○二
父亲和二叔,从来就像休戚与共的亲兄弟,几乎没有红过脸。但是这两个经历诸多磨难终还是拴在一起的把兄弟却为我大吵了一架。
那天,父亲领我去二叔家玩,趁他们拉家常的工夫,我又转到了二叔院儿里的那口大水缸前。这水缸的缸壁雕满了一条条云遮雾罩的赤龙,还刻有凹凸不平但却错落有致的篆体字,很是好看,它一直是我在二叔院里的至爱。我围着比我还高出半头的的水缸转了几圈,就从墙角搬来了一摞砖搁在缸底,踩着攀了上去。当我两腿叉开着浑身发颤地站在缸沿上时,我觉得我神气极了。
这时我忽然憋不住尿了,小腹一阵阵地剧疼,我再也顾不得那么多,解开裤裆,肆无忌惮地尿起来,那黄色的液体哗哗地流进水缸里,立即就被大半缸清澈的水淡化了颜色。正在我得意的时候,二叔和父亲忽然并肩从堂屋里走出来。父亲一看见我那架式,一张脸倏忽变得青紫。他一把将我从水缸上揪了下来,脱下娘做的“千层底”,就在我屁股上没命地抽起来。这时二叔忽然暴躁地大喝一声“你这是干什么,他还是个娃儿!”说着一把夺过父亲的布鞋扔出了墙去,然后将父亲推出门,这才抱起正哭得起劲的我劝慰起来,最后还是用一大捧糖才止住我的哭声。
父亲咬着牙没说什么,阴沉着脸走进院儿去拾起了扁担和木桶,他要去为二叔挑水,但被二叔喝止了。二叔拍着父亲的肩膀说:“娃儿尿一泡尿咋了。他尿了我愿意喝,用不着你瞎操这份心,回家你敢动俺娃一指头,我和你没完……走,喝酒去!”于是父亲踢踏上鞋,跟着二叔向村头那个破旧的小酒馆走去。
○三
光阴似箭,倏忽间物是人非。我渐渐地长大了。当那些幸福的往事变成了模糊记忆时,我才发现二叔老了。作为知识分子的二叔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受过造反派的非难。到现在了,那个岁月所经受的折磨虽然已在二叔豁达乐观的心里淡化的没了痕迹,可是却在他脆弱的肉体下扎了根,每当阴雨天气,他干瘦的腿总是软软地肿胀起来,用手一按一个肉窝。父亲怕他太过寂寞,于是执意要把他接到我家,好有个照应,我和娘也极力地赞成,可二叔就是不允。父亲知道,我也知道,二叔是怕他那满身的疾病连累了我们,这个历尽沧桑的老人,即使满身的疮痍,可善良的心里总装着别人的苦楚。
自从去镇里上了中学,见到二叔的日子更少了。一个大休的日子,我去看望他老人家。那破落的小屋依旧破落,青黄色的梧桐叶落了满院。二叔热情而又感激地将我让进屋里,给我沏一杯浓茶。除了无聊而不实在的寒暄外,我们竟两厢无语了 。两代人,两杯茶,融不进再浓的情中。
看着二叔满头零乱的白发和卷旱烟时微微颤抖的布满青筋的老手,我的心竟痉挛般的悸动了半日。到底是岁月不饶人,老了,我第一次感觉到二叔真的老了。我无法揣磨二叔那时的心情,只能用一颗疲乏的心体会他的孤独和寂寞。
在儿时的记忆中,二叔便拥有一把嗑嘴的茶壶外配一个青黛色的茶杯和一个黑漆斑驳的陈旧的小木盒——里面盛满了干燥的烟叶和纷乱的纸头。十多年了,仍然如故,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杯茶,一袋烟,似乎就是二叔后半生的唯一。我心中涌出一种至今笔头难以表达的凄凉。
我默默地走出了老人的小屋,脑海中回忆着童年的快乐和苦涩。
○四
那些遮在阴隅中的记忆,就在那个多雨的夏天,就在雨雾和泪帘的隔阂中,像二叔嘶哑的喉咙里所挣脱出的哭音,如此现实,如此突然地呈现在我的面前。我扛着父亲的棺木,和二叔一起,像两个虔诚的信徒,大踏步的向远处的群山碧野中走去。我知道,在那一刻,二叔和我一样的心目澄明。
|